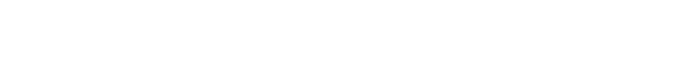□ 王保国
童年时代,最吸引我的就是家门外响起拨浪鼓的声音。当一阵阵“扑棱棱”的鼓声由远及近地传来,这个时候,无论是在大人面前正撒泼哭闹,还是在和小伙伴们一起玩耍,我都会立马抛下眼下的一切,迅速地跑进屋子里,拿上早就准备好的一些“破铺陈、烂套子”以及穿不着的旧鞋、烂鞋底之类的“破烂”,兴冲冲地跑出门外。
那个时候,这些“破烂”对我们来说可谓是“无价之宝”。因为用它可以从走街串巷的货郎那里,换取我们喜欢的一些物品。女孩子用它可以换取红头绳、发卡、雪花膏;我们男孩子常用它换取糖豆、大米团、皮球、口哨、砸炮、玻璃蛋儿等。而年龄稍大些的孩子就有了点文化气息,则常常用它换取小人书、铅笔和本子。有时,家里的大人们也用它换取针线、扣子、手帕等小件生活用品。
在我童年的记忆中,经常到我们村走街串巷的货郎,是一位身材瘦小的老人。夏天气温较高时,老人家除了戴着一顶破草帽遮阳之外,还经常光着被太阳晒得黑黝黝的上身;冬天,他则常戴着一顶火车头帽子,穿黑色棉袄和黑色大棉裤,腰上系着一根棉布条。他的售货车是用木头做的独轮车,木架子、木滚轮,推起时要将系在扶把上的一根布带套在脖子上,躬腰伏背地向前起劲。在他的手推车的两边,各镶着一只用玻璃作盖的木箱,让人一眼就能看清里面装的各种货物,大都是些小孩爱吃的小食品、玩具、生活用品之类。前面堆放的则是他用货物换取的“破铺陈”“烂套子”,旧鞋、烂鞋底儿,生了锈的锄头、铁锨、铁皮等等,应有尽有。
那个时候,只要不是雨雪天,老人大多都会推着手推车到我们村里来。老人家一进村,没人关注时往往先摇一阵儿拨浪鼓儿。随着他的拨浪鼓有节奏的响声,很多人家的大门便吱吱呀呀地打开,拄拐杖的老人、抱着吃奶孩子的媳妇,扎着羊角辫的小姑娘,穿着开裆裤的小男孩。他们手里有的拿着旧鞋底,有的拿着废弃的棉花套儿,还有的拿着妇女剪下来的头发辫子……从四面八方向老人涌去,围成一圈。
一般时候,抢先用“破烂”交易的往往是我们这些年幼的孩子。腿脚麻利,跑得快。大人没到的时候,我们早已经将自己期盼的玩具或小食品换到了手。家中没有“破烂”可置换的孩子,有时也缠着大人掏钱买自己想要的东西。
小时候,我应该就算是那种非常“怪”的孩子吧!用“破烂”完成与老人家的商品交易后,接着,我常常就会趁他不注意的时候,偷偷地抽出他的拨浪鼓,用两只手拼命地摇。老人家是性格相当温和的那类人。看我们玩他的拨浪鼓,他也不心烦。有一次,他正忙着交易,而我与一个大点的孩子对他的手推车产生了兴趣。于是,我们就学着他的样子攥住车把,把布带套在脖子上,用力地向上抬起来。可是,他那个独轮车,一抬起车把,我们就没有力气控制它的平衡了。眼看着手推车倒向一边,吓得我们一阵风似的跑了。后面,老人家气急地喊:“跑不了你们,我去找你们家大人。”话是这么说,但老人家也只是收拾下倒向一边的独轮车就作罢。但此后,我却有好几天都害怕见他,内心有着一种对不起他的感觉。
老人家和他的拨浪鼓的响声,一直伴随着我的童年很多年。而后,也记不清是在什么时候,老人家的背影渐渐地走出了我的视线。
时光慢慢地渐行渐远,如今的乡村,举目都是百货门店、超市。那些众多憨厚淳朴走街串巷的货郎和他们摇拨浪鼓的声音,早已经淹没在了历史的长河中。然而,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我,对那些渐行渐远的记忆,总是心怀着一种深深的情感。那是一个特殊年代的文化符号,更是一种挥之不去的乡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