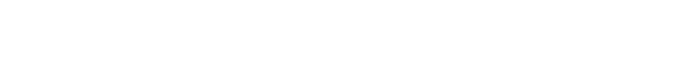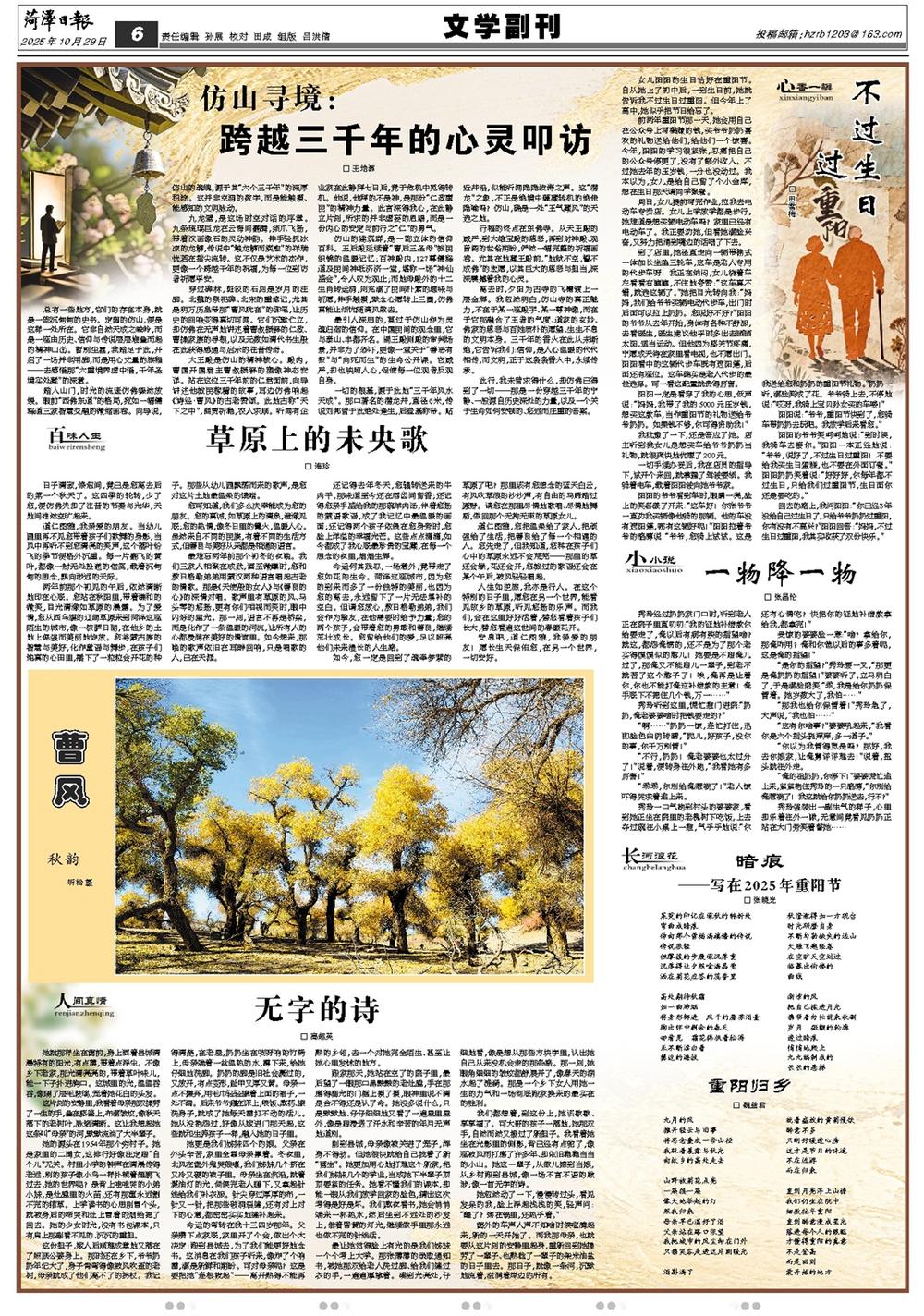□ 高超英
她就那样坐在窗前,身上洒着县城清晨特有的阳光,有点薄,带着点浮尘。不像乡下老家,那光清亮亮的,带着草叶味儿,能一下子扑进胸口。这城里的光,温温吞吞,像隔了层毛玻璃,笼着她花白的头发。
这片刻的安静里,我看着母亲那双操劳了一生的手,叠在膝盖上,布满皱纹,像秋天落下的老树叶,脉络清晰。这让我想起她这条叫“母亲”的河,默默流淌了大半辈子。
她的源头在1954年那个穷村子。她是家里的二闺女,这排行好像注定跟“自个儿”无关。村里小学的钟声在清晨传得老远,别的孩子像小鸟一样扑棱着翅膀飞过去,她的世界呢?是背上哇哇哭的小弟小妹,是灶膛里的火苗,还有那筐永远割不完的猪草。上学读书的心思刚冒个头,就被身后的啼哭和灶上冒着的烟给摁了回去。她的少女时光,没有书包课本,只有肩上那副看不见的、沉沉的重担。
这份担子,嫁人后顺理成章地又落在了照顾公婆身上。那时还在乡下,爷爷奶奶年纪大了,身子骨弯得像被风吹歪的老树,母亲就成了他们离不了的拐杖。我记得清楚,在老屋,奶奶坐在吱呀响的竹椅上,母亲端着一盆温热的水,蹲下来,给她仔细地洗脚。奶奶的脚是旧社会裹过的,又放开,有点变形,趾甲又厚又黄。母亲一点不嫌弃,用毛巾轻轻擦着上面的褶子,一处不漏。后来爷爷瘫在床上,喂饭、熬药、擦洗身子,就成了她每天雷打不动的活儿。她从没抱怨过,好像从嫁进门那天起,这些就和生养孩子一样,融入她的日子里。
她更是我们姊妹四个的娘。父亲在外头辛苦,家里全靠母亲撑着。冬夜里,北风在窗外鬼哭狼嚎,我们姊妹几个挤在又冷又硬的被子里。母亲坐在炕沿,就着煤油灯的光,伺候完老人睡下,又拿起针线给我们补衣服。针尖穿过厚厚的布,一针又一针,把那些破洞裂缝,还有对上对下的心意,都密密实实地缝补起来。
命运的弯转在我十三四岁那年。父亲攒下点家底,家里开了个会,做出个大决定:搬到县城去,为了我们能更好地念书。这消息在我们孩子听来,像炸了个响雷,满是新鲜和期盼。可对母亲呢?这是要把她“连根拔起”——离开熟得不能再熟的乡邻,去一个对她完全陌生、甚至让她心里发怵的地方。
搬家那天,她站在空了的院子里,最后望了一眼那口黑黢黢的老灶膛,手在那磨得溜光的门框上摸了摸,眼神里说不清是舍不得还是认了命。她没多说什么,只是默默地、仔仔细细地又看了一遍屋里屋外,像是跟浸透了汗水和辛苦的年月无声地道别。
刚到县城,母亲像被关进了笼子,浑身不得劲。但她很快就给自己找着了新“营生”。她更加用心地打理这个新家,把我们姊妹几个的学业,当成她下半辈子顶顶要紧的任务。她看不懂我们的课本,却能一眼从我们放学回家的脸色,猜出这次考得是好是坏。我们熬夜看书,她会悄悄端来一杯热水,然后坐到不远处的沙发上,借着昏黄的灯光,继续做手里那永远也做不完的针线活。
最让她觉得脸上有光的是我们姊妹一个个考上大学。那张薄薄的录取通知书,被她那双给老人洗过脚、给我们缝过衣的手,一遍遍摩挲着。凑到光亮处,仔细地看,像是想从那些方块字里,认出她自己从来没机会走的那条路。那一刻,她眼角细细的皱纹都舒展开了,像春天的湖水起了涟漪。那是一个乡下女人用她一生的力气和一场彻底搬家换来的最实在的胜利。
我们都想着,到这份上,她该歇歇、享享福了。可大哥的孩子一落地,她那双手,自然而然又接过了新担子。我看着她坐在光影里的侧影,背已经有点驼了,像座被风雨打磨了许多年、却依旧稳稳当当的小山。她这一辈子,从做儿媳到当娘,从乡村搬到县城,像一场不言不语的跋涉;像一首无字的诗。
她忽然动了一下,慢慢转过头,看见发呆的我,脸上浮起浅浅的笑,轻声问:“醒了?粥在锅里,还热乎着。”
窗外的车声人声不知啥时候喧腾起来,新的一天开始了。而我那母亲,也就要从这片刻的安静里起身,重新回到她操劳了一辈子、也熟稔了一辈子的柴米油盐的日子里去。那日子,就像一条河,沉默地流着,滋润着岸边的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