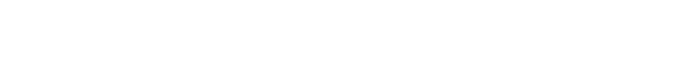□ 张文艳
收拾书房,看到了高准先生己巳之秋(1989年)为我撰书的《仁爱赋》,仔细读来,不禁感慨万千。
高准先生自称孤云高准,祖籍直隶静海(今天津市大港区),1925年8月6日生。工小楷,尤擅微书。父亲高毓彤是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癸卯科进士,入翰林院。高准先生已仙逝多年,在学校时,无论师生,皆称呼高准先生为“高先生”或“高老”。
我1988年9月入校时,高准先生已经退休,但他常于星期六或星期天去学校讲授诗词歌赋,我便有幸成为高先生的学生。虽然时隔卅余年,但高准先生授课时的场景却仿佛眼前。大课堂座无虚席,高先生讲授《诗经》里有关劳动和爱情的内容,是那样地率真而坦荡;先生讲授唐诗宋词的那种凄美与婉约,仿佛自己已是诗词中人。高先生讲授《诗经·将仲子》和李煜的《菩萨蛮·花明月黯笼轻雾》时,写了满满的板书,正好有同学拍摄下来,我也得了一张,留作永久的纪念。
我所在的学校在天津市河东区,高先生的家在南开区,他每次都是乘坐公交车到学校,中间要倒车才能到达。高先生不来上课的时候,也邀请我们去他家里。我和高我一级的隋绍新同学多次去过高先生家,高先生给我们讲他的人生经历,讲诗词里的人物命运。他喜欢花草,记得他家里的窗台上有几株小小的盆花,我说等假期回家带牡丹花送他。他不要大棵的花,他对微弱的生命是那么怜悯和敬畏。他说:“小花草能启迪人生,一粒种子从土壤里萌出,那是生命神圣的诞生。”我记得先生的话,给他带去几粒牡丹花的种子。有一天,高先生告诉我牡丹的种子发了芽,那天真的神态犹如一个快乐的孩童。
记得高先生问我:“什么人可以称为伯乐?”我笑而无言。高先生自己作答:“承认自己跑不过千里马。”这是高先生的谦虚。“人世劳驾旅,死生隔翼纱。百年情未尽,瞬息智无涯。梦享今朝酒,愁看明日花。春风不经意,吹暖万人家。”这是高先生赠我的五言律诗,诗里诗外,充满了人生的哲理与智慧,透彻与旷达。“爱仁者人恒爱,残人者终自伤也。”这是高先生在《仁爱赋》的结言,也是历经沧桑后的人生箴言。记得高先生曾偶然讲起过他的家事。高先生与夫人感情甚笃,夫人去世后,高先生曾恸赋挽诗多章,内有“伤心一步我来迟”之句,即用红楼梦中宝玉悼黛玉之语也。
我在一篇网文中看到高准先生的一位昆曲故友在《突然想起天津南开甲子曲社》文章里有这样的文字:“最后一次见孤云高准是在医院,我和老郭去看他,高准孤零零躺在病床上,身边只有一个护工,经历完翻天覆地的时代变迁,二十年代的大家少爷风流才子,看透世事,只圆睁双眼。最后的最后,他请我们出去,他要清洗身体,礼貌而有尊严地走完这人生的最后一程……而今,风物依旧在,斯人去已远。”
我在天津时,高准先生曾用蝇头小楷为我书写了汉乐府诗《日出东南隅行》扇面,我一直珍藏,今呈眼前,弥足珍贵。高先生德高望重,平易近人,在为我所书文字的落款处全是“文艳同学正之”或“文艳同学雅正”。先生说:“古之有为者,曾以天下为己任,无论华夏夷狄、少长尊卑,并一视而同仁,以为四海之内皆兄弟,不亦宜乎?”这又是怎样的胸襟啊!
人世间,有多少欢乐?多少遗憾?又有多少情愫缱绻?理不清的繁杂,说不尽的恩怨,却似那昆曲里汤显祖《牡丹亭还魂记·寻梦》中言:“这般花花草草由人恋,生生死死随人愿,便酸酸楚楚无人怨”。睹物思人,三十年满腹情感,咏不出恰当的诗篇。恰耳畔是孤云高准先生那文人大家智慧之妙音,眼前是孤云高准先生那慈悲祥和之容颜。
斯人已去,风范永存。庚子春分,谨书此言,以表对孤云高准先生由衷之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