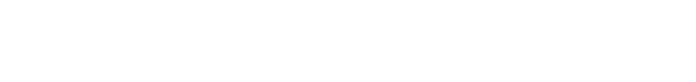□刘言龙
站在秋日的田埂上,风掠过成熟的玉米,送来一阵阵湿润的香气。我凝视着一片片被积水囚困的农田,水光清冷,倒映着这个本应丰收却陷入停滞的十月。这不禁让我想起爷爷口中,那些蜿蜒在田埂间的、早已消失的古老“水道”。
爷爷的故事里,农田从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与沟渠、池塘、河流共生的生命体。那时的排水,并非与自然对抗,而是顺着土地的肌理,进行的一场温柔疏导。过去的雨天,连绵的雨水虽浸润土地,多余的水分会顺着田边挖掘的沟渠,缓缓流向村边的池塘。那些沟渠是祖辈根据地势,顺势而为,那时的大家响应号召,每当农闲时第一要做的事就是挖水沟,每家至少要出一个劳力,扛着锄头、铁锨,仅仅依靠着人力,一铁锹一铁锹挖出一道道水沟,让水流遵循着最古老的自然法则,顺势而下。那时候的大家不懂得挖渠的意义,只知道农田越来越肥,庄稼越来越壮。雨季来临,沟渠会将积水排入池塘,池塘像一块巨大的海绵,吸纳着田里的来水,沉淀下泥土与养分,待到夏日干旱,人们又可把水从池塘引入沟渠灌溉,兼济排涝与抗旱。
以前的沟渠边总是长满野草与芦苇,青蛙在里面产卵,小鱼在水中穿梭,蜻蜓点水,蝴蝶停驻。农人们在劳作间隙,会蹲在沟边洗手洗脚,孩子们则在浅水区摸鱼捉虾。那时的水,是活的,是有生命的。它从天上落下,经过农田的滋养,带着泥土的芬芳和作物的气息,流入沟渠,再进入池塘,汇入河流,完成一次自然的循环。排水,不仅仅是排出多余的水分,更是维系着农田生态的平衡,让土地保持着长久的活力。爷爷说,那时候的土地,哪怕遇到再大的雨水,也从来不会被积水困扰。
然而,随着时光流转,雨水减少了,水渠干涸了,人们盯上了田边的那一点点利益,此后,人们对土地的认知变得单一。沟渠与池塘不再被看作是农田的有机部分,它们被视为“奢侈”的代表,于是沟渠被填平,彻底变成了土地,种上了庄稼。然而,在这份“创收”的背后,我们是否也失去了些什么?那时的我们还不得而知。
后来气候改变,与其说改变,倒不如说是轮回,天气似乎回到了祖辈那时候,雨水开始多起来,人们终于想起了排水沟,可回头才发现,那一道道古老的沟渠早已被填平,积水没了去处,最终积在农田里。那些被填平的池塘、沟渠曾经是农田生态系统的“调节器”和“蓄水池”,它们不仅调节着水量,还净化着水质,滋养着生物多样性。当这些自然的“调节器”消失,农田就变成了一个孤立的生产单元,失去了自我调节的能力,最终淤积溃烂。余秋雨先生在《文化苦旅》中对人类文明与自然关系的思考:我们总是在试图征服自然。但是我们却不明白,即便征服自然,也不过是一时的胜利,最终只会得来更严重的反噬,正确的道路应该是顺应自然。父辈们遵循的是顺应自然,利用自然,而非对抗自然。他们在田埂间留下的,是与土地对话的温柔,是对自然真诚的敬畏。而今天的我们,是否因为过于追求效率,而忘记了这份敬畏?
站在田埂上,风再次吹过,带着一丝凉意。我看着眼前的一亩亩积水的农田,又想起了祖父故事里的那些蜿蜒水道。或许,现在醒悟,为时未晚。我们不应只觊觎水渠下的三分薄地,而应视这整片土地为一份需要世代守护的遗产。水渠,这一圈圈田埂上的年轮,不仅记录着丰收的喜悦,更镌刻着我们对土地的敬畏、智慧与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