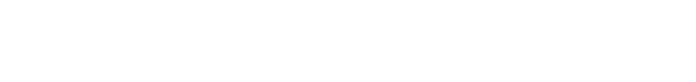□孔伟建
老家院子里,原来有四棵枣树。弟弟结婚那年,因翻盖房子,去了三棵,只剩一棵。多年来,剩下的这棵枣树落单一般,独自坚守着这方院落。看着有些孤单,她早已习惯了这种孤单。
我每次回家,母亲总爱说,这棵树是她嫁过来后栽的,五十多年了,真快啊!五十多年来,这棵树一直站在这里,我想她的根须肯定早已深扎,粗壮。她肯定在暗无天日的地下接着所谓地气,深厚凝重的地气,不可言说的神秘的地气。
跟这棵树差不多年龄的,还有一眼老井。我至今依然清楚地记得当年打井的情形,这井要比树年轻几岁,算来也四十几年了。他俩相距两米远,做了几十年邻居。而今,井水依然清冽甘甜。只是,这棵树近年来开始走下坡路,逐渐呈现老态。不知何年,主干已枯死,又新发几根枝丫,旁逸斜出,每年只是疯长些叶子,不怎么挂果。尽管每年春天枣树开花之时,弟弟都会喷洒些防止落花、有助挂果的农药,却总是不见效果。她的树皮太粗糙了,难用语言形容那种颜色,那是五十多年光阴沉淀下来的颜色,是饱经风霜后的颜色。况且张牙舞爪,长了牙齿一般,让人望而生畏,不敢上手。
想想几十年来,这棵树每年都守着春信,每年都按时开花,那种细小的、密密匝匝的、平淡无奇、其貌不扬的花开得铺天盖地一般,总会引来嗡嗡嘤嘤的蜂蝶,然后会结很多枣子,藏在枝叶之间,孩子般慢慢长大。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如同孩子走向学校、农人走向田野或经营其他生意,如此天经地义。
曾经的苍翠沉浸在明媚的阳光和适时的雨露之中,无数明亮的叶子,仿佛打了蜡一样光滑,微风翻动着它们。喜鹊、麻雀、燕子,还有很多不知名的鸟儿展开翅膀在阳光下飞翔,累了就在这棵树上歇歇脚,然后会有星星点点的鸟粪落在枝叶上。
丰收时节,乡里乡邻多有好吃者,常来我家,在树下仰望一番,然后随手拿起竹竿,瞅准挂果多的地方,打上几竿子,枣叶连同枣子纷纷落地。枣子无需清洗,捡起便吃。爱干净的,在衣服上蹭几下,便大快朵颐起来。
这枣子又大又脆,水灵灵的,青红相间,艺术品一般。熟得好的,通体枣红,落地便会摔出些裂隙,让人想起精美瓷器上那些细若游丝的冰纹。
我出生和成长的那些年,一直跟这棵树相伴,她是家里的日历,她是燕子归来时最早的落脚点和雏燕学飞时的试验站。
枣芽发,种棉花。七月十五枣红圈,八月十五晒半干。庄户人总能从草木之中捕捉到季节变化。每年大雪后,我总忘不了围着她堆一大堆雪,让凛冽的雪水滋润她。每年除夕,我总忘不了将烟花对准她的枝干喷射一番,让她体会火树银花的含义,告诉她人间又是一年。
我一直非常喜欢吃这棵树结的枣子,那种味道和记忆深入骨髓。在老家的那些年,枣子唾手可得。参加工作后,每年枣子丰收,家人总会想方设法给我带点。有时是鲜枣,有时带点熟枣。生枣入口爽脆,味道如一。熟枣软糯香甜,可慰乡愁。
如今,我已逾知天命之年。每个人都有故事,每棵树都是生命。这棵树与我,都在人间经历风吹雨打。心中唯愿这棵树平安,能多伴我一些时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