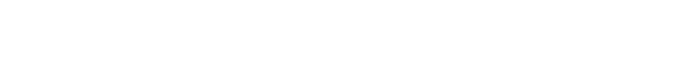作为“单县三宝”之首,单县罗汉参不仅承载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更因明朝时期作为宫廷贡品的显赫身份而彰显其独特价值。由于特殊原因,罗汉参曾一度濒临灭绝。在经历长期的野生状态和人工栽培困境后,经单县罗汉参产业协会会长袁福君等多方努力,罗汉参如今在单县实现了产业复兴,成为名副其实的富民产业和国家地理标志产品。
近日,在单县谢集镇罗汉参种植基地,76岁的袁福君正蹲在田垄间,指尖轻轻拂过罗汉参的根茎。这双手,曾在60多年间抚摸过数十万株罗汉参,也书写了一段从7株野生苗到万亩产业带的传奇。
故事要从1962年说起。当时只有10多岁的袁福君家住单县南城办事处黄小楼村,他在荒野中偶然发现了7株形态奇特的野生植物。“村里老辈人说这是‘土人参’,《单县志》里记载是明朝贡品。”袁福君回忆道。他小心翼翼地将这7株幼苗移栽到自家庭院。
最初的守护充满艰辛。他在自留地里试种,在责任田里摸索,却接连遭遇重创:变压器突发停电,正值灌溉期的罗汉参全部旱死;深井坍塌导致水泵损毁,大片参田因缺水减产过半;最致命的是重茬种植导致的绝收。“看着枯死的参苗,蹲在地头掉眼泪,但就是舍不得放弃。”袁福君的声音里带着倔强。
“罗汉参的根就是它的种子,种过一年的地,十年内不能再种,这是老祖宗传下的规矩,也是产量瓶颈的关键。”袁福君带着问题扎进田间,白天观察生长规律,晚上翻查《农政全书》《本草纲目》里的零星记载。
经过无数次试验,他终于摸索出“轮作倒茬”等一套高产栽培技术,不仅解决了重茬难题,还将亩产从最初的500多斤提高到1000余斤。他研发的“罗汉参规范化栽培技术规程”更是申报了国家专利。
罗汉参产量提高了,袁福君就联合村里几户农户成立合作社,率先在黄小楼村建起种植基地。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如今,单县罗汉参种植面积已扩大至10000余亩。
在单县罗汉参产业园展览馆,一份份检测报告揭示了罗汉参的“养生玄机”:富含16种矿物质元素、17种氨基酸,以及抗性淀粉、西瑞香素等40余种营养成分,尤其硒含量远超普通食材。“这就是它能成为功能性医用食品的底气。”袁福君解释道。
“光会种不行,得让这宝贝走出田间。”袁福君主动敲开山东农业大学、省农科院的大门,带着罗汉参样品恳请专家开展研究。在他的推动下,单县湖西产业技术研究院与多家科研机构联手,证实了其“药食同源”的科学价值。
鲁菜泰斗颜景祥以“罗汉献瑞养生汤”摘得全国金奖。单县头一锅羊肉汤店的老板王振海最懂其中滋味。他慢火炖制的罗汉参雪耳苹果盅,汤色乳白,甜香四溢。现在店里的拔丝罗汉参能拉出两米长的金丝,成了食客必点的“网红菜”。
2013年,“单县罗汉参”荣获国家地理标志农产品认证;2024年,被纳入国家新食品名录。
随着研究的深入,罗汉参的深加工之路越走越宽。在袁福君的倡议下,单县建起了第一家罗汉参加工厂,从最初的简单清洗包装,到开发出粉条、长寿面、罐头等产品,再到如今的功能性口服液、保健品,产品矩阵不断丰富。
在单县罗汉参深加工车间,罗汉参清洗去皮后,有的被切成细条制成粉条,有的被压成粉末做成饼干,还有的经蒸煮杀菌后装成罐头。这些产品将发往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甚至漂洋过海,成为日本茶包的原料。
“种植户每亩年收入是传统作物的3倍。”袁福君翻着订单台账介绍。单县已形成从种植、加工到销售的完整产业链,开发出初级产品、初加工产品、深加工产品、功能性产品和茶系列五大类数十种产品。
暮色为罗汉参产业园镀上金边。在展销中心的玻璃柜中,琥珀色的粉条与泛着黑泥光泽的新鲜罗汉参隔空相望。袁福君摩挲着2024年国家新食品名录证书,目光投向远方的种植基地……
从《本草纲目》的药用记载,到现代餐桌上的养生美食;从明朝宫廷的贡品,到带动万民增收的产业引擎,单县罗汉参这一古老物种,在当代沃土中重焕生机,正为乡村振兴绘就一幅“点参成金”的生动图卷。
记者 仝志华